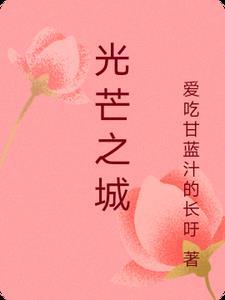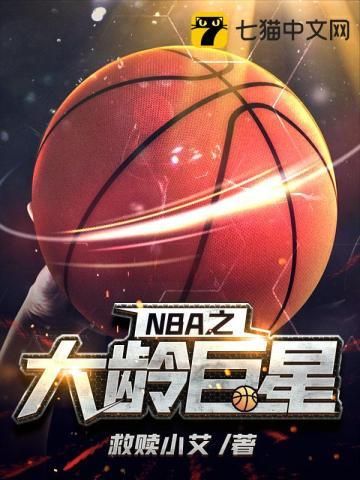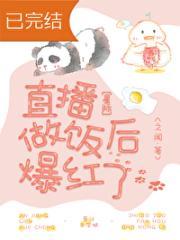穿越小说>伏羲王朝传奇 > 五十结绳记事(第2页)
五十结绳记事(第2页)
“十”
,第二根是麻绳套着鸡毛,上面打着“四”
“十”
。第三根,是麻绳和人黑黝黝的头发,比较粗(男人),打着“二”
“十”
。第四根是麻绳和头发比较细的绳子(女人),上面打着“三”
“十”
。
如果这部落把这些被俘虏的男人杀死,只要在那第三根代表二十个男人的绳子上,用鲜血涂上,就代表这“二”
“十”
个“男人”
被“流血”
(意指死亡)了。
然而“古者无文字,其为约誓之事,事大大其绳,事小小其绳。结之多少随物众寡”
(《易九家言》)的记录方式,仅靠绳结大小记录大小事,而无关事件的内容,而且事件的大小量级很难有确切的界限。这种随意性将有违文字记录语言“其为誓约之事……各执以相考”
(《易九家言》)的目的。随意性就意味着怀疑和思想上的混乱,社会的稳定就会出现问题。
因此诸如用绳结大小和象形式的编织绳结不仅手法复杂,其一致性也难以统一。这种方式肯定得不到认可和推广。然而仅仅靠“事大大其绳,事小小其绳。结之多少随物众寡”
这样解释,有些语焉不详,失之笼统。因为事物是复杂的,只打大小结,并不能表明所打之结是记的何事。或许短时间内还能想起所打之结是记的什么事,而时间一长,所打之结增多,就很难记清若干大小不等的结各记的是什么事了。
结绳记事的语言表述组成就如同语言由元音和辅音组成一样,有了“结”
这个元音,加以辅音“节”
,模拟了声音的长短不同,在结绳记事中进行表现,也就是说结绳记事有结也有节。从而可以形成在一段绳子上“结、节”
的组合。这一组合就使得简单的结在节的调节下出现了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
的复杂变化。只有具备了这样功能的结绳记事手段,才能完整表述语言,才会有管理社会化部落的能力,让治理部落的诺言可考和可重复验证的契约成为可能。从而达到“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以书契,百官以治,万民以察”
(《易·系辞下》)
这样,就出现了与所述事物比较相似图形的结绳记事,事实上,这也是后来象形文字最先的形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