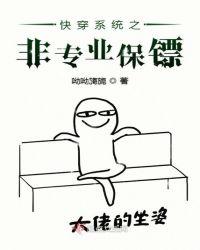穿越小说>重生七零豪门霸妻 > 第73章 通向世界的路(第1页)
第73章 通向世界的路(第1页)
蒋红梅踩着高跟鞋冲进实验室时,颜良丰正在调试显微镜,竹制算盘搁在一旁,算珠上还沾着晒干的药粉。搪瓷缸里的野菊在冒着热气,却不见颜珍珍的人影。
“珍珍呢?”
蒋红梅的声音里带着少见的急促,旗袍开衩处露出的小腿绷得笔直,像是随时要拽着谁逃离某种宿命。
“去药材田测土壤湿度了。”
颜良丰摘下眼镜,镜片上倒映着墙上的《茂村药材种植规划图》,“红梅啊,你先喝口野菊茶,这是今年头茬花。。。。。。”
“别跟我绕圈子!”
蒋红梅将机票拍在实验台上,紫荆花图案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光,“听说她打算毕业后回村?你这当爹的也不拦着?当年我们拼了命想离开的地方,她怎么就。。。。。。”
话音未落,门“吱呀“推开,颜珍珍抱着土壤样本闯进来,蓝布衫下摆沾着新泥,额角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,像撒了把亮晶晶的碎钻。
蒋红梅一把拽过颜珍珍的手腕,珍珠耳钉在日光灯下划出凌厉的弧线:“珍珍,我听李明辉说,你毕业后要回茂村?”
“暂时的呀,”
颜珍珍将土壤样本轻轻放下,“得先把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起来,等土壤改良数据稳定了。。。。。。”
“打住!”
蒋红梅拍着实验台,震得天平砝码叮当作响,“什么暂时不暂时?你可是中医学科最拔尖的苗子!当年我们知青点多少人拼了命想离开农村,你倒好,主动往回钻?”
她故意忽略姑娘瞬间瞪大的眼睛,将烫金录取通知书拍在桌上,又从皮质手袋里掏出张机票,“香港大学的交换生名额,我托人给你留着,下周立马就走。“
颜珍珍的指尖深深陷进土壤样本袋,湿润的泥土从指缝溢出,染黄了她掌心的茧。那些茧是去年在烘房里守夜时磨出的,每一道都嵌着野菊花的细屑。“红梅姨,茂村的标准化种植刚有起色,药材深加工的配方还在调试。。。。。。”
她的声音像浸了水的宣纸,柔软却坚韧。
“这些我来盯着!”
颜良丰突然开口,布满老茧的手掌拍在实验台上,震得搪瓷缸里的菊花上下浮动,“你只管去读书,那些想浑水摸鱼的客商、打秘方主意的人。。。。。。”
他从中山装内袋摸出个铁皮盒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与外商的谈判记录,“爹替你挡着这些明枪暗箭。”
蒋红梅望着眼前的父女,忽然想起十几年前的雪夜——颜良丰也是这样把一块红薯塞进她的饭盒,用冻得发紫的嘴唇说“你先吃。”
此刻,他鬓角有了白发,却依然挺直着脊梁,像极了后山那棵历经风雨的老菊王。
“珍珍,“颜良丰放软声调,轻轻握住女儿的手,指向窗外渐暗的天空,“现在的茂村需要的,不是一个守着土地的姑娘,而是一个能站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专家。“